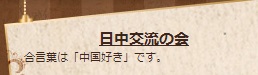莫邦富的日本管窺(229)大平正芳获奖和中国日语教育的“黄埔军校”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尽管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受到世界评价的。
最近中国政府向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100人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奖章,以示表彰。同时,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日本人2名。他们是“国际知名企业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
我觉得日本的获奖人选非常精准和令人信服,尤其是大平正芳使我想起了中国日语教育的黄埔军校“大平班”。这是因为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的提议而开设的一个日语培训机构,我是大平班的第一期学员。
进入新世纪时的日本由于经济长期在低迷的谷底中挣扎,找不到走出困境的出口。因“失去的十年”而引起普遍的焦躁情绪,以致对ODA(日本政府为发展中国家设立的政府开发援助)的议论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中国ODA援助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从1979年开始的对华ODA援助,到上世纪末已达2万4500亿日元。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提供ODA已无必要,应当大量削减援助金额和改变援助重点。甚至有极端论调认为,日本的对华ODA援助得不到中国的感谢,完全是一种浪费。
当时,我觉得这种论调和视点不对,于是在日本『中央公論』杂志2001年4月号上写下《请记住“大平学校”》一文,指出:对ODA在日中相互理解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被无视而倍感遗憾。
文章首先回顾了大平班的诞生过程。
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问了中国,日中两国间确认,有必要进一步促进交流。特别是作为在文化领域里合作的一环,决定为促进中国的日语教学而展开合作。
当时,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路线,学习日语的人数急剧增加,日语教师成了到处争抢的对象。
但由于多年的锁国政策,中国的日语教师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
日本了解到当时中国有日语专业或日语课程的大学有37所、日语教师约600人,遂决定以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为中心,从1980年8月开始在北京语言学院内设置日语研修中心(在中国的正式称呼是“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以中国各地大学里的这600名教师为对象,实施为期五年的日语研修项目。这就是“大平班”的由来。只不过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项目后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那时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任教。1980年8月,我作为第一期学员,与8名同事走进了北京语言学院的校门,开始在大平班开始为期1年的日语进修。
5年中,来自160多所大学的594名日语教师分5期,在大平班接受了长达1年时间的日语进修。这些大学涵盖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大平班走出去的学员们日后成了支撑中国日语教育大业的“绿色的山脉”,以致有人说大平班是中国日语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大平班在日文中被称作“大平学校”,正式的“日本语研修中心”或“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这2个称呼反而不怎么使用。因为人们对文革时期走向极端的个人崇拜之风非常不满,80年代在中国是很少有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组织或团体的。据我所知,在日本的援助项目里,以日本人姓氏冠名的项目只有大平班一例。
不仅是在大平班里学习过的学员还是日本人教职员,甚至连中国政府官员也是这样称呼,可见大平班的影响有多大。
1985年,当这一为期5年的援助项目顺利结束时,中国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女士赞不绝口地说:“大家都亲切地把这个研修中心叫作‘大平班’。在中国的日语教育界都知道有个‘大平班’,还受到日本教育界的很高评价,真不愧是中日友好的结晶。”
她还明确表示感谢说:“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向为实施这一项目做出努力的日本政府、外务省以及国际交流基金表示感谢。”
而实际在大平班进修过的近600名中国学员及执教过的近百名日本讲师的感受则更为感人。当时学员们拼命学习,每天要自修学习到熄灯为止,星期天也都用在自习上。11号楼是学员的宿舍,每到夜晚,各个房间里都泻出煌煌的灯光。
这种对中国学员来说是极其自然的学习态度,却使日本的老师们大为感动。5 年中一直担任大平班主任(校长)的佐治圭三教授20年后与我重逢时已年过70,但回忆起大平班岁月时,却仍然目光熠熠。
“我在大平学校的5年里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岁月。那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5 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第一期学员们的那种朴素而纯真的、充满学习意愿的眼神,我感受到了在日本的教育现场完全体验不到的那种感动。”
名古屋大学平井胜利教授也说:“当时大家都是干劲十足,所以特别值得怀念。直到现在,我都能立即说出第一期120名学员每个人的姓名、长相、走路的姿势。”
学员们的认真学习,对来自日本的教师们来说居然成了无形的压力。佐治教授因过于劳累而住进医院时,都顾不上休息,躺在病床上辅导年轻教师。担任第一期课程的5位年轻的日本女教师一到夜里就聚集在一起自修和备课,房间里的灯光也是不到深夜不熄灯。
可以说,来自日本的教师们是以一种献身精神来进行教学的。从第二期到第五期一直在大平班讲课的早稻田大学的竹中宪一教授为了提高学员们的外语听力,不止一次放弃星期天的休息,上午八点就来到教室给学员们进行外语听力补课,整整4年这种自发性的补课从没有中断过。
回日本后任职于东京学艺大学的谷部弘子教授回忆说:“像许多教师一样,我也是在大平班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筑波大学的平冈敏夫教授只教过4个月,他也说:“在北京的4个月是我的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最美好的日子。4个月的时间中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真是说也说不完。”
佐治教授在病床上辅导年轻女教师、平井教授隐瞒病情指导学员学习、年轻教师们自发进修到深夜……,这些情况作为学员的我们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20年后我知道了这些详情时依旧心头阵阵发热,再一次体会到感动是不会过期的。
大平班的毕业生后来有的当上了中国的大学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日语教育学会会长、学科带头人,成为中国日语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有不少人活跃在日本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致力于日语的普及。
曾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负责大平班项目的小宫山猛1985年秋谈到大平班成功的原因时说:
“我从事了将近29年的文化交流事业,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有成果的事业。大平班的业绩将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熠熠生辉。我确信,大平班为面向21世纪的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当年外务省为宣传ODA的必要性而编写的对华援助概要书中,对1979年以来的各类援助项目做了细致入微的记述,却丝毫没有提到大平班。这使我甚至一度怀疑大平班使用的经费不是来自ODA这一基本事实了。为此,我给国际交流基金去电话确认。得到的回答明确无误:“是ODA,是ODA,没有错!”
我当即感到一阵茫然。许多日本人谴责向中国提供了ODA却得不到中国人的感谢,而许多中国人一直怀抱着感谢之情的ODA援助项目却被日本人自己抹掉了。
1979年起近4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ODA援助达3.65万亿日元,而在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留下这么大影响的大平班,所用去的10亿日元的经费却只占ODA总额的3650之一。
创办大平班的提案人、现已故去的大平正芳首相曾经这样说过:“仅仅建立在追求经济利益之上的友好形同砂上楼阁。人与人之间只有心心相印才会结成真正的友好关系。”
而提出这样主张的大平正芳去世那么多年后还能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充满感谢之情的奖章,正是对上面所说的那段话的最好注解。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tearoom/33608-2018-12-21-01-47-42.html/?n_cid=NKCHA014
最近中国政府向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100人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奖章,以示表彰。同时,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日本人2名。他们是“国际知名企业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松下幸之助、“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大平正芳。
我觉得日本的获奖人选非常精准和令人信服,尤其是大平正芳使我想起了中国日语教育的黄埔军校“大平班”。这是因为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的提议而开设的一个日语培训机构,我是大平班的第一期学员。
进入新世纪时的日本由于经济长期在低迷的谷底中挣扎,找不到走出困境的出口。因“失去的十年”而引起普遍的焦躁情绪,以致对ODA(日本政府为发展中国家设立的政府开发援助)的议论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中国ODA援助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从1979年开始的对华ODA援助,到上世纪末已达2万4500亿日元。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提供ODA已无必要,应当大量削减援助金额和改变援助重点。甚至有极端论调认为,日本的对华ODA援助得不到中国的感谢,完全是一种浪费。
当时,我觉得这种论调和视点不对,于是在日本『中央公論』杂志2001年4月号上写下《请记住“大平学校”》一文,指出:对ODA在日中相互理解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被无视而倍感遗憾。
文章首先回顾了大平班的诞生过程。
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问了中国,日中两国间确认,有必要进一步促进交流。特别是作为在文化领域里合作的一环,决定为促进中国的日语教学而展开合作。
当时,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路线,学习日语的人数急剧增加,日语教师成了到处争抢的对象。
但由于多年的锁国政策,中国的日语教师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
日本了解到当时中国有日语专业或日语课程的大学有37所、日语教师约600人,遂决定以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为中心,从1980年8月开始在北京语言学院内设置日语研修中心(在中国的正式称呼是“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以中国各地大学里的这600名教师为对象,实施为期五年的日语研修项目。这就是“大平班”的由来。只不过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项目后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那时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任教。1980年8月,我作为第一期学员,与8名同事走进了北京语言学院的校门,开始在大平班开始为期1年的日语进修。
5年中,来自160多所大学的594名日语教师分5期,在大平班接受了长达1年时间的日语进修。这些大学涵盖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大平班走出去的学员们日后成了支撑中国日语教育大业的“绿色的山脉”,以致有人说大平班是中国日语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大平班在日文中被称作“大平学校”,正式的“日本语研修中心”或“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这2个称呼反而不怎么使用。因为人们对文革时期走向极端的个人崇拜之风非常不满,80年代在中国是很少有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组织或团体的。据我所知,在日本的援助项目里,以日本人姓氏冠名的项目只有大平班一例。
不仅是在大平班里学习过的学员还是日本人教职员,甚至连中国政府官员也是这样称呼,可见大平班的影响有多大。
1985年,当这一为期5年的援助项目顺利结束时,中国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女士赞不绝口地说:“大家都亲切地把这个研修中心叫作‘大平班’。在中国的日语教育界都知道有个‘大平班’,还受到日本教育界的很高评价,真不愧是中日友好的结晶。”
她还明确表示感谢说:“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向为实施这一项目做出努力的日本政府、外务省以及国际交流基金表示感谢。”
而实际在大平班进修过的近600名中国学员及执教过的近百名日本讲师的感受则更为感人。当时学员们拼命学习,每天要自修学习到熄灯为止,星期天也都用在自习上。11号楼是学员的宿舍,每到夜晚,各个房间里都泻出煌煌的灯光。
这种对中国学员来说是极其自然的学习态度,却使日本的老师们大为感动。5 年中一直担任大平班主任(校长)的佐治圭三教授20年后与我重逢时已年过70,但回忆起大平班岁月时,却仍然目光熠熠。
“我在大平学校的5年里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岁月。那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5 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第一期学员们的那种朴素而纯真的、充满学习意愿的眼神,我感受到了在日本的教育现场完全体验不到的那种感动。”
名古屋大学平井胜利教授也说:“当时大家都是干劲十足,所以特别值得怀念。直到现在,我都能立即说出第一期120名学员每个人的姓名、长相、走路的姿势。”
学员们的认真学习,对来自日本的教师们来说居然成了无形的压力。佐治教授因过于劳累而住进医院时,都顾不上休息,躺在病床上辅导年轻教师。担任第一期课程的5位年轻的日本女教师一到夜里就聚集在一起自修和备课,房间里的灯光也是不到深夜不熄灯。
可以说,来自日本的教师们是以一种献身精神来进行教学的。从第二期到第五期一直在大平班讲课的早稻田大学的竹中宪一教授为了提高学员们的外语听力,不止一次放弃星期天的休息,上午八点就来到教室给学员们进行外语听力补课,整整4年这种自发性的补课从没有中断过。
回日本后任职于东京学艺大学的谷部弘子教授回忆说:“像许多教师一样,我也是在大平班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筑波大学的平冈敏夫教授只教过4个月,他也说:“在北京的4个月是我的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最美好的日子。4个月的时间中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真是说也说不完。”
佐治教授在病床上辅导年轻女教师、平井教授隐瞒病情指导学员学习、年轻教师们自发进修到深夜……,这些情况作为学员的我们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20年后我知道了这些详情时依旧心头阵阵发热,再一次体会到感动是不会过期的。
大平班的毕业生后来有的当上了中国的大学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日语教育学会会长、学科带头人,成为中国日语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有不少人活跃在日本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致力于日语的普及。
曾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负责大平班项目的小宫山猛1985年秋谈到大平班成功的原因时说:
“我从事了将近29年的文化交流事业,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有成果的事业。大平班的业绩将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熠熠生辉。我确信,大平班为面向21世纪的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当年外务省为宣传ODA的必要性而编写的对华援助概要书中,对1979年以来的各类援助项目做了细致入微的记述,却丝毫没有提到大平班。这使我甚至一度怀疑大平班使用的经费不是来自ODA这一基本事实了。为此,我给国际交流基金去电话确认。得到的回答明确无误:“是ODA,是ODA,没有错!”
我当即感到一阵茫然。许多日本人谴责向中国提供了ODA却得不到中国人的感谢,而许多中国人一直怀抱着感谢之情的ODA援助项目却被日本人自己抹掉了。
1979年起近4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ODA援助达3.65万亿日元,而在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留下这么大影响的大平班,所用去的10亿日元的经费却只占ODA总额的3650之一。
创办大平班的提案人、现已故去的大平正芳首相曾经这样说过:“仅仅建立在追求经济利益之上的友好形同砂上楼阁。人与人之间只有心心相印才会结成真正的友好关系。”
而提出这样主张的大平正芳去世那么多年后还能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充满感谢之情的奖章,正是对上面所说的那段话的最好注解。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tearoom/33608-2018-12-21-01-47-42.html/?n_cid=NKCHA014

2018-12-21
第四届肿瘤统合治疗学术研讨会在东京大学圆满落幕
2026-01-06
滞在相談顧問:帰化した中国人の訪中
2026-01-03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通过《人民中国》发表新年贺词
2026-01-02
《中文导报》2026新年献词:穿越寒潮 护送温暖 照亮新年
2026-01-03
新年賀正
2026-01-02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
2026-01-01
滞在相談顧問:中国人同士の日本国内での婚姻手続と婚姻の証明について
2025-12-31
北海道中国工商会・北海道中国会共催「新春交歓会」のご案内
2025-12-30
客观日本12月号(四)可选择性攻击大肠癌的海洋细菌,治疗效果显著
2025-12-26
中文导报:北海道中国会举办年会暨恳亲会
2025-12-24
客观日本12月号(二)日本科技补充预算案全貌公开
2025-12-12
东瀛万事通・今日头条・中文導報・日本东方新报:北海道中国会举办第十二届总会&恳亲忘年会
2025-12-11
第12回 北海道中国会 総会&懇親会
2025-12-07
客观日本12月号(一)THE更正世界大学排名,东京科学大学升至第166位
2025-12-02